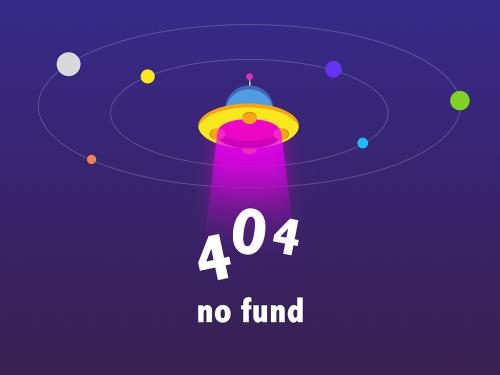杜大伟、黄益平、姚洋: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与内部挑战

2012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项长远的发展目标:到2049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 周年之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繁荣富强的国家。鉴于中国自1978年起推行经济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所取得的成功,要实现这种变化当然是有可能的。但变革之路道阻且长,存在不少不确定性因素。
中国国内面临着很多挑战,比如:人口老龄化、城乡差距、薄弱的金融体系、创新力不足和依赖碳基能源等严重的国内挑战。此外,中国与一些主要凯发官网首页的合作伙伴的对外经济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导致双方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在不断加大。我们在《中国 2049》一书中探讨了一系列政策,可以帮助中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人口老龄化
新冠疫情向我们发出了一个警示,从现在开始到2049年,可能会有层出不穷的不可预知事件发生。但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将快速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代。目前,中国的总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每名女性生育1.7个孩子,远低于2.1个孩子的更替率。中国的生育率之所以下跌,原因可能是中国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但政策的松动并未让普通家庭选择生育更多孩子。中国和其他许多人口密集的亚洲国家一样,住房和教育成本高昂,很多夫妇选择只生一个孩子,或者根本不生孩子。即使生育率有所提高,但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而言,20 年内,其影响杯水车薪。
中国人口总量可能已达顶峰。更重要的是,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在未来几十年,老年人口预计将大幅增加(见图1)。到 2049 年,中国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增加1倍之多,达到 4 亿人。届时,中国将面临的更突出问题是,85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将增加两倍多,达到约1.5 亿人,超过美国和欧洲此类人口的总和。在处于工作年龄段的群体中,唯一将上涨区段介于 55— 64 岁 。

人口老龄化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照顾老年人需要全社会向医疗保健、长期护理和疗养等领域投入更多资源。按照中国的传统,老人一般由子女赡养。但是,由于家庭规模变小,许多老年人在晚年时可能会无人赡养。将以前由个人承担的老人赡养成本社会化,既有人道主义意义,也有经济意义。
新冠疫情暴露出了中国医疗卫生系统所存在的优势和劣势。优势在于,中国可以进行大规模的临时动员,将稀缺资源转移到最紧急的地方——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快速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但很多中国人现在认为,国家有必要加强卫生服务体系,充分利用医疗资源,特别是在老年人聚居的农村地区。
尽管内部存在挑战,但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不一定预示着中国劳动力数量会急剧下降,劳动力数量还取决于劳动参与度。特别是,中国需要改革退休年龄政策,逐步提高劳动力的退休年龄:男性公务员可以在60岁退休,女性公务员可以在55 岁退休。如果身体健康,多数65岁以上的老年人会选择继续工作。政府还可以推行家庭友善政策,这会提高和维持女性劳动力的参与度。
城乡差距
中国城镇化的脚步伴随着40 年的改革发展进程稳步向前。城市人口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不断增长着,占总人口的数量从改革之初的20% 增长到了现在的60%。其中,有2亿多的农民工在现有户籍制度下仍保留着农村户口。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活力以及生产率增长很大程度上都源于这种人口流动,但人口流动本身却面临着诸多限制。如果在经济低迷时期失业,这些农民工一般会选择回到农村。当这些新移民来到城市时,他们无法充分享受到城市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因此,也很难带着子女或父母一起到城市中来生活。其结果就是形成了割裂的家庭,父母在城市工作,爷爷奶奶守着家里的农田,抚养着留在家乡的儿童。
中国的城市户籍限制政策正在逐步取消,尤其是在一些二、三线小城市。如江西省最近取消了户籍限制。但在广州和上海等中国最发达的经济中心地区,户籍限制政策依然很严格。虽然中国存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但城乡收入比仍在稳步上升。到 2007 年,城镇职工的人均收入已达到农村地区的3.14 倍——这使中国成为了全世界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见图2)。中国人口大约占全世界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但却只有7% 的可耕种土地,因此,想要5 亿人口摆脱农村经济、过上小康生活,困难重重。不过,即便算上已经迁入城市的农民,相对于中国的人均收入和人口密度来说,中国的城市化率仍然很低。韩国等经济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在这个发展阶段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 80%。令人欣慰的是,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贫富差距有所缩小——不过这种差距还很大,城镇职工收入是农民收入的 2.71 倍。

中国如果完全取消户籍限制,会产生巨大收益。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农村人口中的儿童和老年人比例过高。城市汇聚了大量优质学校,可以让未来的劳动力人口有机会接受更加优质的教育。虽然一些老年人更愿意留在农村地区,但也有一 些人会希望搬迁到城市中生活,离他们的成年子女更近一些,同时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从经济角度来说,农村地区仍存在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放宽落户政策有助于维持城市的劳动力人口。
多一点融合,少一些壁垒
关于中国的成功,一直有一个有趣的悖论, 那就是,它的金融体系不发达,但却实现了快速增长。一项基于银行所有权、利率监管、信贷分配干预和跨境资本流动管制的“金融压抑”指数显示,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金融压抑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类似于印度,略高于俄罗斯和南非,其自由化程度也远低于发达经济体。一直到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金融体系几乎完全处于管制状态,从 1980 年到 2000 年左右,中国的金融体系才在自由化方面取得了较好进展,但自此之后就停滞不前。
对此,我们的解释是,向金融自由化迈出的最初几步轻松化解了中国经济所存在的问题,将中国的大量储蓄导入到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在当时的发展阶段,适度的金融压抑有助于确保资金成本维持在较低水平。在出口和房地产行业,贷款都需要实物抵押(财产、建筑物、机械设备),因此,信贷分配并不困难。中国的出口主要来自私营企业,而非国有企业。房地产开发和房屋所有权也都属于私人性质。因此,政府出台鼓励发展出口和房地产产业的政策, 实际上是间接地将资源引向了私营企业。
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 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这段时间,是中国的黄金成长期。新增贷款快速增加,gdp 较快增长完全可以维持非金融部门债务与 gdp 等指标的稳定。然而,这一切在 2008 年发生了改变。为了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维持市场需求,中国开始向地方政府和钢铁行业等以往由国家主导的上游产业放贷, 以此大举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决定向重点国有企业倾斜更多资源,希望通过资源和政策的倾斜,帮助它们成为全球龙头企业。中央政府下放给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贷款激增,导致经济体中的负债总额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就表示,中国的金融体系在新的市场环境下表现得不是非常理想。如果融资推动的投资产生了强劲的增长效果,那么,债务与 gdp 之比将保持稳定或缓慢上升。但杠杆率的快速上涨表明,资金多数流向了低效投资。
近年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停滞,凸显出资本配置能力薄弱这一问题。全要素生产率 衡量的是生产率增长中无法由劳动力或资本增长 解释的部分。在21世纪头十年初期,中国政府的大规模直接投资帮助建立了国内私营制造业产业,此后,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增长 2.6%,且在头十年后期加速至3.9%,引人瞩目。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再未出现强劲增长,2015年至 2019年期间的年增长率为 0.2%。
生产率停滞不前也释放出了一个信号,即中国需要加大创新力度,建立多元化的金融体系,为创新提供助力。中国存在许多有助于创新的元素:国内市场潜力大;研发投入占比高(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 2.4%);每年提供数百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和软件开发人员;逐步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但中国的创新产出明显与这些优势不符。中国在一些技术领域的进步令人印象深刻,如金融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但经济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疲软。中国仍在向国有企业倾斜大量资源,然而,大多数发明专利却来源于私营企业。
中国的金融体系更加青睐那些拥有传统资产(建筑物、机械设备)的企业,但对于那些依托 于知识产权且富有活力的初创企业,则不愿为其提供资金。中国在对其下一个五年计划做出微调时,应将工作重心放在加强融资等领域的创新生态系统,而非针对特定行业和技术给予政策扶持。特别是中国还承诺在 2060 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所以创新是实现国家环境目标的关键。
扩大贸易和投资
中国的人均 gdp 能否赶超发达经济体,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继续融入全球贸易和投资市场当中去。中国几乎是从完全自给自足的状态发展成为了如今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2020 年,中国还成为规模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然而,当前的国际环境极具挑战。中国计划在特定科技领域形成领导地位,令其凯发官网首页的合作伙伴产生了担忧情绪,反过来,这些凯发官网首页的合作伙伴对中国的科技企业施加了贸易和投资限制。在此背景下,面对着可能出现的风险,中国随之提出和制定了“双循环”战略, 突出了内需和国内创新的重要性。技术脱钩不仅会伤害中国,还会对全球生产率增长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
作为反制措施,最近 ,中国签署了几项重要的经济协定,例如与亚太地区国家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与欧盟签署的《全面投资协定》。中国还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成员国就未来加入该协议展开了对话,这一切都需要中国政府做出重大改革,例如,限制对国企的资源倾斜和补贴,向外国投资开放全新行业。中国还向拜登政府建议,减少两国经济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壁垒。
成败主要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国内挑战。
总之,中国正处于对外经济关系的拐点上。继续全面开放本国经济,开展贸易和投资协定磋商,这些都对中国具有深远意义。但成败主要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国内挑战。人口老龄化和城乡差距互为关联:加深融合有助于中国满足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的需求,防范本可以避免的城市劳动力人口急剧下降这一问题。金融改革与创新政策也互为关联。从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转向广泛扶持的创新产业,需要中国政府建立起一套更加多元化、更加富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不再一味给予国有企业政策倾斜。想要减少碳排放,同时又不影响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关键在于创新。
文章刊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金融与发展》 2021年6月号,原英文文章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杜大伟:布鲁金斯学会约翰 • 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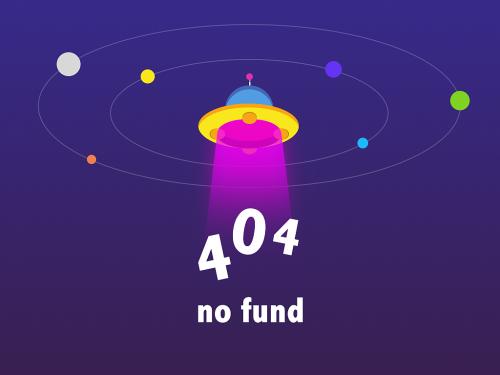
黄益平: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姚洋: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