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吾道不孤
相关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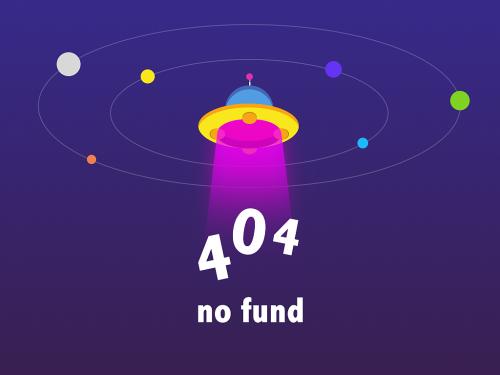
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自己讲了许多话,也听了同事、朋友、同学们讲了很多关于我的话。此时此刻,我内心里只有三句话。第一,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第二,我内心充满了感激。第三,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群人。
首先,为什么我是很幸运的人?我深深地感受到我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幸运的大时代里, 1952年我出生的台湾非常贫穷,在成长过程中我目睹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奇迹。1979年我刚到大陆的时候,大陆比我出生时的台湾还贫穷,我来后大陆经济飞速发展,让我再次目睹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
中国的发展奇迹,让我有幸到世界银行工作,站在小时候从来不曾想象过的国际舞台上。那几年我经常访问世界各地贫穷落后的国家,考察非洲的农村时不禁让我想起小时候住在小县城里,暑假到舅舅家里去帮忙做点农活,放牛、在田里捡稻穗的影像不时涌现心头。有几次非洲农村的小孩,看到世界银行的副行长来了,一群大人陪着,他们跟随在后用充满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小时候我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舅舅家的村子里偶尔会有地方的小官来视察,村里的大人前呼后拥,我曾经也是跟随其后看热闹的许多小孩之一。我常想今天非洲那些小孩将来会不会像我一样,有机会受到比较好的教育?有机会看到生他们养他们的国家摆脱贫穷?有机会走上国际舞台?如果我不是成长在台湾和大陆这样一个大发展的时代,我自己会不会是在台湾一个小县城里面庸庸碌碌的人?我的下一代会否还是跟随在大人后面看热闹的小孩?我有幸生于贫穷,长于欣欣向荣的大时代,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的小孩,他们没有像我这样的幸运,他们可能生于贫穷,长于贫穷,甚至也死于贫穷!
生活在两岸中国这个大时代里不只是我一个人,能得到各位今天的赞誉,反思自己一路走来,最主要是我从小就有了很多在关键时刻——用我们台湾话讲——牵成我的“贵人”。我是一个有六个孩子的家庭排行当中的小孩,上有兄长、姐姐,下有妹妹。我特别幸运,小时候不仅得到父母格外的呵护,而且兄长、姐姐也无私地帮助我,在我受教育、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已经工作了,会省吃俭用给我买书、给我零用钱,照顾我、鼓励我。
结婚成家后,天涯旅居,聚少离多,妻子无怨无悔地一路跟随。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对父亲也特别谅解。就像各位刚才讲的,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我的办公室经常是朗润园里的最后一盏灯,常年回到家里已是凌晨之后,孩子都已经熟睡了。他们读小学时,必须在五点起床七点赶到学校上早自习,多年是住在同一个屋子里,一个星期难得见一次父亲的面,他们没抱怨过我没有像其他父亲一样陪他们做作业,参加家长会。
我成长的过程中,从小学开始,到中学、大学,老师们也都格外给予了我关心、帮助。我特别感激小学时的李锡楼老师,是他发现了我这只丑小鸭;中学的莫凯老师让了解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民族悲哀;如果没有芝加哥大学舒尔茨教授的慧眼,我大概不会成为一名经济学家。
我在工作上也得到了很多同事和朋友的帮助。从台湾军校毕业后到了部队当连长,当时的营长让我认识到青年人的当担。到了大陆后,得到了许多领导的关心,特别是1982年接到舒尔茨教授的邀请到美国读书时,大陆领导能够以培养人才的胸怀放行。从美国回来,当时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杜润生老先生,今天早上锡文已经讲过了,以老一辈革命家的胸怀来接受一位从海峡对岸过来的年轻人,给予信任和重用。在发展所的同事,包括当时的所长王岐山和锡文、杜鹰、其仁等同事不把我当作外来的人。开始时,我确实像今天上午杜鹰所讲,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如果说我现在对中国经济问题把握得比较好,都是在发展所那几年的共事中从他们那里补了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最欠缺的一课。在发展所工作时,我同时也在北大兼职当副教授,平新乔、孙来祥等当时也都正处青春年华的同事一起试图推动北大经济学教育的革新。
后来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其他几位创始同事对中心的发展做了诸多贡献。双学位的构想是易纲提出来的,海闻作为主管行政的副主任设计了许多制度安排,维迎给国内带回了博弈论,后来其仁、国青、卢锋的加入提升了政策研究的水平,大源的无私奉献才有了mba和emba的项目,解决了中心持续发展所需的资金。张佳利、邢惠清、赵普生、行桂英、陈曦等给中心打造了一个服务教学科研的行政文化。正是这样一群有共同的情怀、责任和抱负的青年人,才能够创造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段历史。
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得益于很多朋友的帮忙,蔡昉和李周是我早期的主要研究伙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郜若素、德来斯戴尔,香港科技大学的郑国汉、雷鼎鸣,国内的韦森、张军、史晋川、巫和懋、张晓波、鞠建东、文一等则帮我在切磋中前进。同样重要的是学生们,从他们那里我获得了教学相长,刘明兴、张鹏飞、胡书东、盛柳刚、陈斌开、徐朝阳等为我在芝大的约翰逊讲座和在剑桥大学的马歇尔讲座提供了许多帮助。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后是徐佳君、王勇、付才辉、陈曦的同心协力、全神倾注,才能够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产生了国内国外的影响。
要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时代和这么多人的帮助,不可能有今天的我。上个月,《解读中国经济》第十种语言版,阿拉伯语版在阿联酋的国际书展上发布,主办方举办了一个对话会,和我对话的是阿布扎比的文化局局长,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说这本书结构宏伟、逻辑清晰,特别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问我是如何写出来的。我回答其实这本书不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中国,我写这本书,去做那些研究,是为了帮助我自己了解中国,写出来后我很高兴在帮助我自己了解以后,也能够帮助其他人了解中国。作为一位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我何其有幸得以两次亲历人类历史上的增长奇迹,在帮助我自己了解这些奇迹背后的道理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成败的经验时,我积累了许多和现在主流理论不一样的观点,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我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我希望这些研究也能够帮助世界上许多仍然深陷贫困陷阱的国家找到一条走向繁荣的道路,我衷心希望前面提到的曾经跟在我后面的那些非洲小孩也能够生于贫困长于欣欣向荣。
今天这个会最让我高兴的是让我有了“吾道不孤”的喜悦,从上午到现在各位的发言中,我觉得我们有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的共同认识,我很高兴大家都赞同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今天与其说是庆祝我回国任教30周年,我倒觉得今天是在座的各位以及我自己的一个新的起点,大家一起推动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贡献中国的智慧于世界,“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我们现在做的才刚刚是一个起点,未来的天地会更宽广,未来的成就会更大。虽然说我今年65岁,按现代人的标准还只是青年,但和在座的许多同学们比,就像毛主席曾经讲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今天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未来的世界是属于中国经济学家,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世界,尤其是年轻学者的世界。
谢谢!
本稿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原创,转载请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