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我与ccer
相关附件:
(一)
2013年7月5日,国家发展研究院在朗润园致福轩教室举行一年两度的教授会,院长姚洋说2014年要举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二十周年庆典,商量庆典日期时有老师问真正的院庆究竟应该是哪一天,结果在场的几位元老似乎达不成一致的意见。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听到的一个说法:历史往往是由活得最长的那个人决定的。好在ccer的史料工作做得还不错,哪一天学校批准成立筹备小组,哪一天任命了中心主任、副主任,哪一天又正式召开成立大会,这些具体的事件在官方网站的大事记里写得清清楚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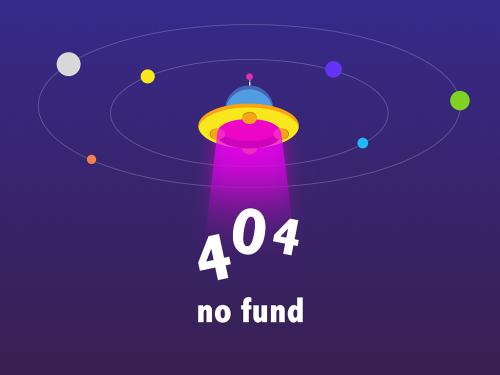
我没有参与关于院庆日的讨论,我加入ccer才四年,其中还有两年请假离开,资历上没法跟很多资深教授比。但我也算是出席过“一大”即ccer成立大会的。当时我到巴黎出差之后来北京开会,我和太太入住南门外酒店时因没带结婚证还遇到了一点小麻烦,正好林毅夫老师到酒店看望参会代表,向酒店作了口头证明才算过关。ccer筹备期间我刚刚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交了博士论文,当时林毅夫老师去澳洲访问时问我是否愿意回来,他还说了一个道理:如果现在回来,你就可以成为北大的老师。但再过十年、二十年,即便是美国顶级大学毕业的博士也不一定能进得了北大。那时我导师郜若素正好也给我提供了一个研究员的职位,他很支持我回国,不过建议我先留在澳洲积累一些论文发表。很多年之后再回首,不得不承认林毅夫和郜若素都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人。
这样看来,我在ccer的资历很浅,但渊源却并不浅。2013年底我在北京郊区九华山庄参加一个活动,会前跟海闻聊天提到像我这样新来的老师,海老师打断说你不能算新来的,你也是老人了。顿时让我有了一种即便没有参加过“一大”也肯定列席过遵义会议的感觉。有一次开会姚洋总结ccer的两个历史传承,一个是留美经济学会,另一个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ccer的首两任主任林毅夫和周其仁都曾经是发展所的主将,而我是国发院教授中除林、周之外唯一在发展所工作过的正式员工。要是这么算的话,那朗润园能跟我比资历的教授人数应该不会很多吧。
我毕业之后跟着郜若素教授一起做的第一个项目是关于中国粮食政策的研究,当时我们还邀请海闻和卢锋分别到堪培拉访问了三个月。记得海闻做的是关于农业保护政策的分析,而卢锋则完成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提出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以劳动密集型食品换土地密集型食品的主张。两人做的研究都很有意思,但性格反差十分鲜明。卢老师发现堪培拉环境优美,有不少有共同兴趣的学者,可以静下心来做研究,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海老师则常抱怨这个地方天黑之后一片死静,生活相当无聊,在堪培拉访问期间他出去开了好几次国际会议。
1996年9月开始我到ccer访问了三个月,当时中心有一个世界银行访问学者项目,鼓励海外学子短期回国交流,提供每月一千美元的生活费外加一张机票。那段时间林老师和海老师都不常在,易纲在中心主事。因为做国企改革研究,我跟张维迎有交流,之后还邀请他去堪培拉参加了国企改革的研讨会。1996年的时候ccer还没搬到朗润园,在地学楼一层占了两间半房间,大一点的一间做教授们共用的办公室,小一点的一间是三位行政人员的办公室,朝北较暗的半间算是会客室。访问学者没有办公室,只好到行政办公室转悠,趁哪位老师不在座位上,赶紧借其电脑查一下电子邮箱。
ccer给我安排了临时宿舍,南门附近一个老式筒子楼里的一个朝北的单间,里面全部的家当包括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脸盆和一个热水瓶。好在我一个人生活很简单,唯一不方便的就是晚上上洗手间。办公室的邢惠清老师一家三口跟我邻居,隔一个屋。不过他们家有电话,有时候有人打电话到他们家找我,邢老师就派她儿子汉超来叫我。那个时候汉超好像才五、六岁,跟我交情不错,我离开的时候,他亲自画了一幅画给我做告别礼物,那张画在我们澳洲家里的冰箱上贴了很多年。等我后来回到北大工作时,汉超已经成为北大医学院的学生,还选修过我为经济学双学位开的货币银行学。
现在不记得在ccer的三个月间具体做了什么研究,但好像参与了不少事务性的事情。1996年是ccer第一年招收研究生,当时中心人手不足,从本校招进来的曹雄飞担当了很多行政工作。记得新生报到那天,我还去三角地附近帮助迎新,后来跟几位同学相对熟悉。还有一次是ccer派我去外经贸部研究所参加一个会议,现在不记得具体讨论的什么问题,同去的有在中心帮忙的两位管理系的学生吴旭华和邓海燕,还有一位管理学院的年轻老师。记得第二年大学毕业后,吴旭华加入了汇丰银行,邓海燕则远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读博士。
几年之后我离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到花旗工作,虽然离北京的距离近了,行业却隔得远了些。不过和ccer的联系一直保持着,2005年年初我负责的区域从大中华区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第二年把当时在ccer工作的沈明高挖到花旗做中国经济学家。有好多次我们带着客户来朗润园见林老师或卢老师,求教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每次开完会表示感谢,林老师总会说,自己人不用客气,令我们十分感动。不过那段时间见得最多的可能还是海老师,非典闹得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胡永泰教授在日本组织“亚洲经济研讨会”,我和海老师都写了论文分别自香港和北京赴会。在东京开会那几天,由于没有非典的危险,感到十分的轻松。海老师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永远充满激情的工作热情,几乎每次见面他都会兴奋地描述即将展开的或大或小的工作。
(二)
我是2009年6月1日正式到朗润园工作的,我上班的第一天就被要求在致福轩教室给一个培训班讲课,那天正好是美国财长盖特纳到万众楼二楼做报告,所以给我的要求是课间不休息,不要让学生随意在园子里溜达。当天在盖特纳的讲座上有一位北大元培的本科生张博洋问了一个问题,关于中国在美国国债市场巨额投资的安全性。后来我在货币银行课上提到这件事,张博洋正好也在班上,之后他还选了我为研究生开的国际金融课程,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毕业以后经我推荐到康纳尔大学跟着国际金融问题专家prasad教授读博士去了。
虽然之前我没有在朗润园正式工作过,但跟部分老师已经比较熟悉。林老师是我在发展所时的领导,我去澳大利亚留学就是林老师给的机会。2008年下半年我考虑回国工作时给林老师打的电话。当时他已经在世行任职,正好在北京参加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成立仪式。周其仁老师是当年发展所的学术灵魂,也一直是我仰视的人物。跟周老师一起聊天是一件特别愉快的事情,尤其是听他讲在东北套熊、养鹿的经历,相当精彩。有的故事来回听过多次,每次听都觉得很有意思。至今觉得最不可思议的还是周老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为非党员参与起草中央文件,然后回单位听领导传达文件的经历。
朗润园还有很多在学生中和社会上都有相当号召力的老师,比如汪丁丁、卢锋和姚洋等。不过我觉得最神奇的还是宋国青,当年我在发展所的主要工作是研究、试点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我们那个方案的基本思路就来自宋老师在北大读本科时做的一个分析。我到朗润园的时候,宋国青已经作为“中国宏观经济预测第一人”名震江湖很多年。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表示很难听懂宋老师讲课,往往要过后才能慢慢体会到他的功夫。但只要他开讲,一定满座,以至于每次开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卢锋总是把宋老师安排到最后发言,保证能够留住听众。有一次我主持宋老师的讲座讨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他做了各种测算,最后得出三个结论,潜在增长率可能提高了,也可能下降了,但也可能没什么变化。
新任院长姚洋,被誉为经济学界的梁朝伟,其魅力之大,可想而知。不过跟梁朝伟一样,在日常生活中姚洋是一个比较闷的人。他已经毕业的学生有一次跟我说,跟姚老师在一起呆着很容易冷场,一开始很不适应,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发现了一个窍门,那就是要冷得住,他不说话,你也不用说话,过一会儿姚老师就会找话头跟你说话。相比较而言,我跟胡大源的渊源更深一些。他是人大农经系79级本科,毕业后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是1984年到农经系跟张象枢老师读硕士,1987年毕业到发展所工作。胡大源也是张老师的学生,不过是1988年毕业,所以我一向把他视为师弟。有一次聊天我提到这事,大源颇不服气,当场提出不同意见,说他1983年开始就跟张老师一起讲课了,那时我还没来人大,显然其资历应该排在我的前面。没办法,后来一次聚会,我请张老师裁定究竟谁是师兄,可惜张老师似乎也不太认同大源是我师弟的说法,算是留下一桩历史悬案。
朗润园的资深教授在江湖里的名头都很响,其实最活跃还是一批年轻老师,不但研究做得好,在学生中都拥有庞大的粉丝群。李力行的足球、徐建国的篮球、沈艳的生活哲理,学生中的影响力很大。斯坦福毕业的计量老师黄卓,平时很有幽默感。加入朗润园之后第一次参加教授会,会后老师们在直隶会馆聚餐。当时两桌人点了一瓶白酒,我倒了特别小的一杯给坐在邻桌的黄桌,他说他不会喝酒,我说不会喝酒没关系,我也不喝酒。不过按照国发院的规矩,新来的同事必须把这一小杯干掉。听我这么说,他就没再表示什么。过了一会大家发现他满脸通红,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不过朗润园最让我吃惊的是里面的工作人员,个个身手不凡。我在花旗的时候有几个特别能干、负责的助手,离开的时候我想以后大概很难再有这样的同事,一到朗润园我就发现我错了。汇丰银行有一个叫马晓萍的中国经济学家,当时不认识,只知道是从ccer出来的,后来才知道她以前是院里的科研秘书。我到朗润园工作时的科研秘书叫王姣,她在安排课题和组织会议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办事能力极强。有一次聊天她说想出国读一个学位,但不想搞学术,我说那我推荐你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吧。选择专业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她说想学公共政策,感觉数学要求会低一些。结果对方教授说经济学那点数学怎会难倒你一个北大物理学院的毕业生?结果一年下来八门课程门门都是最高分。学校赶紧给了全额奖学金让她接着读博士。现在再见到我不再提最新游戏软件,跟我讨论央行的货币政策问题。现在帮助我组织格政的卢婧,不但负责、能干,国内客人来了她用中文接待,美国客人来了她用英文接待,法国客人来了她还能用法文接待。
当然在朗润园的主要工作还是和学生打交道。国发院派给我的教学任务是一门本科生的课、一门研究生的课和一门mba的课。给本科生主要是介绍基本知识,给研究生就需深入研究问题,给mba学生则要求理论联系实际。不同的学生要求不一样,很有挑战性。尤其是给“后emba”上课,分寸拿捏要求很高,校友曲菲曾经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理论深不得,深了听不懂;实际浅不得,浅了没兴趣。给本科生的课是大课,四百多人,说实话交流不容易,我只好通过定期请学生吃饭、夏天集体吃雪糕、冬天集体吃冰糖葫芦和课前讲笑话的方式增强交流,曾经还发生了有男生利用讲笑话的机会公开表白的事情,虽然这位男生最后没有成功,但还是给大伙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日常打交道最多的还是我自己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这些学生也是几乎一人一个故事。我到朗润园招的的第一个博士生王勋,来找我时只剩下两年时间,不过他还是按期圆满地完成了博士论文,还发表了不少文章。第二批博士生陶坤玉、王碧珺和林念,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手头都很快。但最刻苦的当属王碧珺,几乎天天都能在图书馆见到她,出了很多活,还没毕业已经成了“著名”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专家。第三批博士生的差异性相当大。沛初特别诚恳,戴黎非常独立。开始的时候苟琴有点内向,不过后来变得相当开朗、自信,发表了不少文章,也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与他们同届的两位硕士研究生彭旭和党韦华,综合素质都很高,毕业之后去了金融机构工作。
(三)
朗润园汇聚了一批享誉海内外的经济学家,有的宁静淡泊,“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矢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以说朗润园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地方,不过二十年前林老师、海老师、易老师等创始者就决心要让ccer成为国内经济学教学、科研和智库三个方面标杆。按这些标准来衡量,朗润园应该说还是做得不错的。ccer老师们引进的一些做法,比如开办经济学双学位和夏令营招研究生等,已经被国内许多大学效仿。我在2009年加入朗润园之后随中国开放基金会的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团里一位国防大学的青年老师说朗润园就是青年经济学子眼中的麦加,这个说法令我深受震撼。
到朗润园工作之后,经常有人问各位教授之间有不同看法如何协调。我说不需协调,君子之争,不伤和气。“和而不同”其实是健康的学术环境的表现。比如我根据自己的分析提出的中国经济改革期间采取的是不对称的市场化策略的思路,最初是从宋国青关于统购统销的分析受到启发,但宋老师并不完全赞同我的框架。前几年大家分析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问题,我和张晓波的研究支持中国已经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结论,但姚洋和卢锋的研究则认为中国农村依然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再比如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但姚洋认为中国政府实际执行了大部分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建议。
朗润园的各种学术思想有没有一个公约数?如果有,或许可以总结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八个字。所谓有效市场,就是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和制度障碍,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这也许进一步引出是否存在一个“朗润学派”的大问题,当然这个话题最好留给有兴趣的学者来总结)。这个主张十分清楚地反映在教授们在各个领域提出的改革建议。即便是十分重视政府作用的林毅夫,仍然强调政府的所有政策都应该以动态比较优势为基础。多年前宋国青率先提出市场决定汇率的重要性,林毅夫曾经对于违背比较优势的大飞机生产战略提出了疑问,周其仁提出的以确权和流转为核心的土地改革的主张,以及卢锋对发改委调控过剩产能政策及其效果的分析,背后都有一条如何尊重市场、让供求关系发挥更大作用的核心思路。
当然,朗润园的教授们尊重市场并不奇怪。但大多数教授认为政府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比如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和提供公共服务,再比如克服市场失灵。政府不能替代市场,但政府需要发挥作用补充并改进市场运作的效率。国内经济学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改革成功并不是因为政府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政府放了什么。把所有的改革成果都归结为“放”,“一放就灵”,放得越多越好。这些极端的市场化言论听起来很有道理、也很过瘾,但是否符合中国实际,只能是见仁见智了。但起码有一条,世界上比中国政府管得少的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前苏联、东欧的改革采取休克疗法,比中国放得更彻底,但它们的经济表现似乎都赶不上中国。
2014年1月22日,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我国第一份《中国智库报告》。根据这一报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分别在经济政策研究、政治建设研究、文化建设研究、生态文明研究和城镇化研究等五个重要领域排名中进入前五位,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庞大的官方机构并驾齐驱。朗润园获得这样的承认并非意外,二十年来,国发院的老师积极参与了包括国企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电信改革、加入世贸组织、土地制度改革和汇率改革等几乎每一场政策讨论。
ccer成立二十周年,起码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件大事情,值得大张旗鼓地总结、纪念并庆贺一下。过去二十年,我的角色主要是作为ccer的朋友站在跑道边上鼓掌,现在有幸作为朗润园的一员,就写个短文表示祝贺吧。



